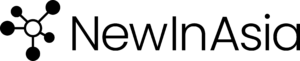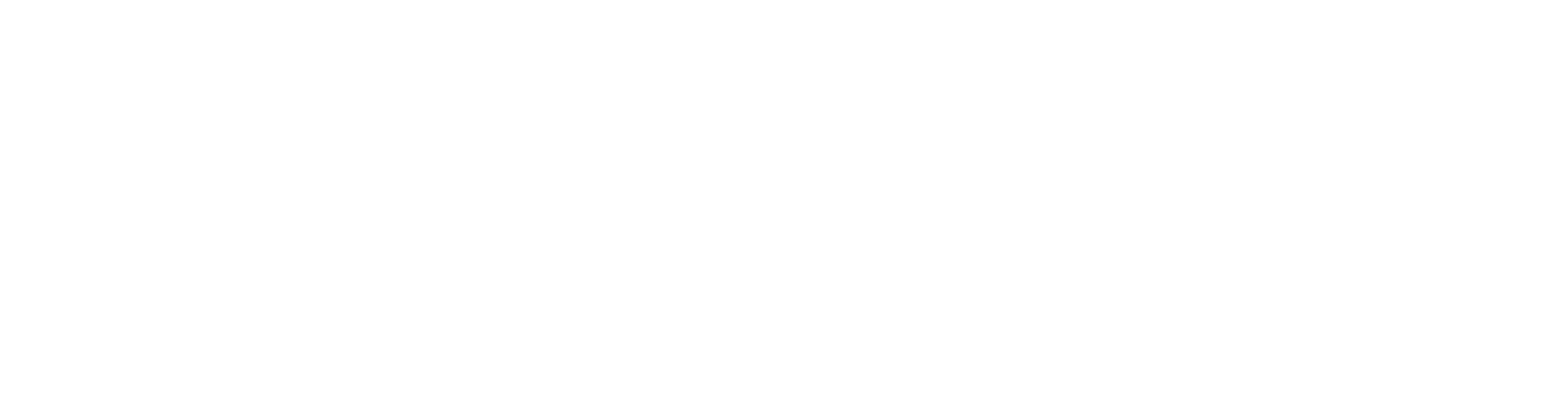在关闭了新加坡首批可变资本公司(VCC)基金之一后,Mike Sim 深刻反思:基金经理为何应更坦诚面对基金关闭的过程——以及整个行业该如何重新定义“有原则的领导力”。 亮点基金关闭的不言现实治理比光鲜更重要从痛点中提炼使命:我的体悟培养新一代基金领导者重新定义基金管理的“成功” 基金关闭的不言现实 在亚洲蓬勃发展的基金生态中,我们热衷于庆祝基金的成立、融资成功,以及季度业绩超预期的表现。然而,在这些高光话题之外,有一个被严重忽视的现实:当一个基金结束运营时,我们该如何面对——特别是,它并非因为失败而终止,而是为了坚持原则而主动退出。 几年前,我做出了一个艰难却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:主动关闭我创立的可变资本公司基金(VCC)。当时,我是新加坡最早根据金管局(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)新制度推出该类基金的人之一——而我可能也是首位自愿将其关闭的基金经理。从表面看,这像是一种“后退”;但对我而言,这是一次治理层面的决定。 我们的基金架构已不再适应其不断演变的发展方向。继续运营就意味着要降低我对运营标准的要求,而这是我无法接受的。因此,我选择关闭它——悄然、负责、并不张扬。这不光鲜,但却是正确的决定。 治理比光鲜更重要 真正令我惊讶的,并不是那繁复的法律与行政流程(虽然确实繁琐),而是这个过程缺乏行业支持与前例。整个行业都懂得如何高调庆祝基金的成立,却几乎没人教你如何体面地退出。 这个经历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:大多数关于基金管理的教育,并没有为专业人士提供应对真实运营挑战的能力。要么是高屋建瓴的理论框架,要么是密密麻麻的监管备忘录。但这些都无法指导你,在合规瓶颈耗费投资人信任、市场变化快于你基础设施响应速度时,该如何做出判断。 鲜有人讨论如何配置团队、如何与托管机构和律师合作,甚至是如何在不陷入数月等待的情况下开设银行账户。而这些“操作层面”的细节,才是真正决定一个基金能否可持续的关键。 从痛点中提炼使命:我的体悟 在关闭我的 VCC 过程中,我体会到一个残酷的事实:哪怕结构良好的基金,也可能因执行层面的摩擦而失速。尽管我们拥有优秀的投资线索和明确的策略主张,但合规与客户接入的延误,让整个节奏失去了动力。看似稳健的架构,终究还是败在了现实面前。 我没有选择默默离场,而是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——包括那些盲点、忽略的细节、以及那些从未有人提前告知的昂贵教训。很快我意识到,这些问题并不只出现在我身上,而是整个行业的系统性缺陷。 这些反思,成了我如今工作的基础:为新晋基金经理、转型中的金融专业人士和合规人员提供辅导与培训。我们不谈抽象理论,而是揭示真实场景下的应对方式——帮助他们在压力之下做出更明智、更有韧性的决策。 培养新一代基金领导者 我所指导的专业人士,往往聪明、上进且富有经验,但却对基金结构缺乏深刻理解。他们擅长谈业绩,但一提到股东权利、赎回机制或审计周期,答案就开始模糊了。 这并不是能力的问题,而是金融行业在人才培养上的结构性缺陷。我们的行业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,推崇规模却忽略架构。 如果我们想要打造更强健、更具韧性的亚洲私人市场,就必须重新看待“治理”的价值。它不应被视为后台功能,而是一种核心领导力。而现在,是时候以这种标准来培养下一代基金人了。 重新定义基金管理的“成功” 基金关闭之所以多在沉默中进行,是因为它与传统的“成功叙事”不符。但为了正确的理由选择离场,并不等于失败,而是成熟的领导力体现。 我最自豪的时刻,并不是成立基金的那一刻,而是当我指导的一位专业人士,在真正理解基金机制后,拿到了改变其职业轨迹的岗位。这样的影响力,远比包装华丽的故事更有价值——清晰胜于虚荣,使命重于光环。 亚洲金融的未来,不仅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者,更需要真实、坦率的领导者。如果我们想培养具备未来竞争力的基金人才,就必须把整个故事讲完整——包括那些关于关闭、复杂性与勇气的章节。 编者按:本文为 Mike Sim 的特约稿件,发表于 NewInAsia 的《领导力与投资战略》专栏,聚焦亚洲新兴市场中具有洞察力的从业者观点。文章观点为作者个人所有。若您希望分享关于领导力、创新或治理的观点,请联系 NIA 编辑团队。 亮点基金关闭的不言现实治理比光鲜更重要从痛点中提炼使命:我的体悟培养新一代基金领导者重新定义基金管理的“成功” Read the English article here, or listen to the podcast here….